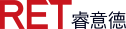“去商业化”的趋势下,该如何重新理解“商场”的定义?
消费降温,是危机,也是提醒。设想这样一个极端场景:人们一夜之间集体按下“暂停键”,商场里没人买单,直播间空空如也,物流中心罕见清闲。
这不是反乌托邦小说的情节,而是J.B. MacKinnon在《当世界停止消费》中抛出的核心命题——如果全世界的人不再购物了,我们将如何生存?
听起来像危言耸听,但别忘了,疫情那年我们已经经历了它的雏形。那一年,消费被迫降速,世界也并没有坍塌。
于是问题来了:如果未来的某一天,消费者不是因为封锁,而是因为不再需要、不再渴望、不再盲从而选择不消费,购物中心还能靠什么活下去?
这是一个极端假设,也是一个现实的提醒,是商业赛道玩家值得思考的未来问题。
消费,曾是购物中心的全部
当“停止消费”从一种极端设想变成现实语境的可能时,回头看购物中心的运营逻辑,我们不难发现:它几乎全部建立在“人必须持续消费”的前提上。
曾几何时,购物中心是消费主义的神殿。货架设计、动线规划、坪效计算、品牌更迭,每一个细节都围绕“转化率”展开,消费者来这里,是为了“买”——越多越好,越快越妙。我们理所当然地默认:商场是“消费容器”;品牌要抢“黄金位置”;活动=折扣=转化。
购物中心的成功指标,归根到底就是“买了多少”。但这一切的逻辑,正在被瓦解。理性消费成为主旋律,“空手逛街”在社交平台上热度飙升,年轻人越来越倾向“看得见但不拥有”,“在场”但不购买。
问题不再是人来不来,而是人来了为什么不买?
购物中心销售逻辑的矛盾点:

©RET睿意德中国商业研究中心
《当世界停止消费》给了我们一个思考命题
加拿大知名作家J.B. MacKinnon在《当世界停止消费》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,看似极端,却无比真实:如果有一天,全世界的人都不消费了,我们会变成什么样?
这本书不是对消费的否定,而是对消费惯性的拷问。在作者构建的实验性场景中,社会并未崩溃,反而出现了以下变化:城市空气指数显著改善,垃圾填埋速度放缓,自然生态开始复苏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回归质朴,人类个体重新思考“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”。
他甚至指出:“消费的暂停,不是灾难,而是一种新秩序的可能性。”而对于购物中心来说,这是一道赤裸裸的提醒:如果我们把商业空间的全部意义,都绑定在消费这一个动作上——当这个动作终止,整个空间就会失语。
从这个角度看,“不消费”不是威胁,而是一面镜子,照出购物中心是否具备真正的内容力、场景力和情感联结力。
“消费暂停”带来的价值反问:

©RET睿意德中国商业研究中心
当消费不是目的,空间还能承载什么?
重新回到购物中心这个物理空间,我们可以换个问法:除了交易,购物中心还能提供什么?答案是很多的,甚至比“买东西”更有价值:
1. 提供城市关系连接点
情侣约会、朋友聚会、亲子陪伴、独处时光,商业空间早已承担了“关系场”的功能。
2. 情绪与感官的调节站
咖啡香、手作坊、艺展馆、沉浸式装置……那些留得住人的空间,从来都不靠SKU,而是靠情绪。
3. 表达价值观的公共界面
户外环保、宠物友好、性别平权、新手艺人……购物中心也可以是城市精神的放大器。
换句话说,如果购物中心只为消费而生,那它注定会在消费理性化的浪潮中逐渐失语。但如果它是一个情绪、关系与文化的交汇场,它的存在感就会超越交易本身。
商业空间的新旧功能对比:

©RET睿意德中国商业研究中心

不是不消费,而是“换种方式在消费”
别误会,消费者不是不花钱了,而是变聪明了。
他们:不追新品,但愿意为设计感、可持续、品牌理念买单;不囤货爆买,但愿意为一场好展、一杯有故事的咖啡花钱;不在乎打几折,更在乎“我是谁”、“我属于哪里”。
这就要求购物中心的运营逻辑从“货-场-人”转向“人-场-内容”。
内容是什么?是能引发共鸣的主题展览、音乐现场;是围绕兴趣聚集的微型社群和互动空间;是让用户参与共创的品牌、活动、策展机制。

©RET睿意德中国商业研究中心

从“人买东西”到“人与内容发生关系”
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,早已不是靠“打折清仓”维生,而是用“内容即场景”的方式,创造非消费驱动的吸引力:
日本涩谷PARCO百货的复合型空间,集合了漫画、科技、独立设计师品牌与开放式咖啡馆,每层楼都像一次文化旅行,即使不买东西也会来“泡上一天”。
韩国首尔的The Hyundai首尔店,其地下层变身“城市公园”,草坪、流水、音乐和书店并存,零售区被自然氛围包裹,访客停留时长远高于其他商场。
荷兰阿姆斯特丹的De Hallen则将废弃电车车厂改造为城市生活复合体,内含图书馆、电影院、工坊、跳蚤市场、共享厨房,人们来这里不是“血拼”,而是“生活”。
这些项目的共通点在于:消费不再是目的,而是顺便发生的结果。
购物逻辑VS内容逻辑:

©RET睿意德中国商业研究中心

如果不消费,那我们该运营什么?
这是对所有购物中心运营者的一次灵魂叩问。我们要运营的,不只是“卖场”,而是: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机制,城市生活方式的样本空间,多元文化的交汇舞台,心理松弛与归属感的发生地。
国际上已有不少案例对此做出回应:
法国巴黎的Le BHV Marais,原本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百货公司,在消费放缓的大背景下主动转型,引入手工坊、宠物体验空间、花艺课程等,使其成为年轻人社交与兴趣联结的重要场域。品牌销售不再是主目标,参与感成为主要价值。
澳大利亚墨尔本的Emporium Melbourne在近年投入巨资重构“非购物体验”,将原本用于时尚零售的空间改造成共享厨房、可租赁摄影棚和本地内容创作者孵化器,使购物中心与城市创意经济发生连接。
德国柏林Bikini Berlin提出“概念商场”理念,将传统租赁关系转化为“空间共创合作”,由品牌、艺术家、顾客共同决定空间的形态与内容。商场内大量空间用于实验性装置、快闪剧场、青年共创展览,消费退居其次,文化成为主角。
这些案例背后的共同逻辑是:运营的是生活的关系,而非商品的流通。只有当购物中心本身成为“有意义的空间”,消费行为才可能再次自然发生。
新旧运营指标的对比:

©RET睿意德中国商业研究中心
结语
如知名社会学家马塞尔·莫斯所言:交换行为从来不只是经济行为,更是社会关系的具象化。在数字化浪潮和消费代际更迭的双重驱动下,这个被称作“商场”的实体空间正经历着深刻的重构。过度商业化的环境已无法满足后物质时代的需求,人们开始寻求超越实用功能的“深层次游戏”。唯有突破“商业中心论”的认知框架,这个“场”才能真正成为城市部落的现代栖息地;而空间摆脱了“商”的符号暴力,“场”才能回归其本质——成为承载集体记忆、塑造身份认同、完成社会整合的现代“神圣空间”。这或许正是数字时代实体空间存续的终极答案:从交易场所蜕变为意义生产的文化装置。